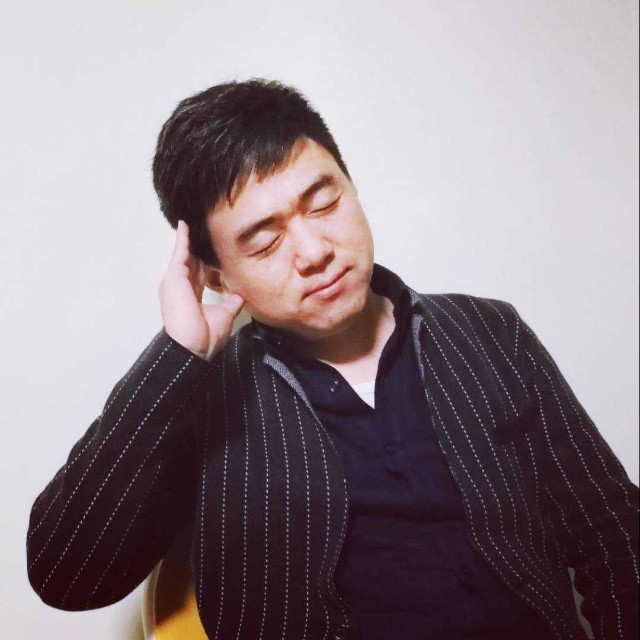01
群体理性与个体非理性
一看到“群体理性”这个词,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勒庞所写的《乌合之众》。
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群体经常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后来的心理学实验,如耶鲁大学在二战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也证明了“盲目服从”模式的存在。因此,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群体的非理性行动”这个概念。
今天这篇文章里提到的“群体理性”,其实是指当每个人独立决策时,最终在统计学层面上呈现出的一种理性分布。
比如,我们对所有感冒患者采取的措施进行统计,会发现有人选择硬扛,有人喝点白开水,有人会用感冒药。
而在用药的人当中,大部分可能会用针对轻症的中成药,只有少数人会用药效较强的西药,甚至去医院治疗。于是,我们便得出了群体在面对感冒问题时的理性统计数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体理性”。
但事实上,每个独立的个体在感冒时,又会做出各种各样非理性的决策。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回想一下疫情放开初期,当我们自己感染新冠病毒时,是如何处理的?
我们并不会完全理性地只看院士或知名专家的建议,我们还会受到身边同事的症状严重程度,以及他们家人是否因此遭受重创等情况的影响。
如果身边有重症,我们就会特别重视,甚至吃好几种药;而如果身边都是轻症,有些人即便费尽心思抢到了几片退烧药,也可能一片都不用。
所以,我们今天要阐述的,就是这种群体理性与个体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主要想聊一聊“价格”这个具备物理属性的要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02
从消费者流转看价格趋势
拜伦·夏普教授(Byron Sharp)在他那本名为《How Brands Grow》(中文译名《非传统营销》)的书中,用大量数据得出了一个结论:消费者是“花心”的,或者说品牌忠诚度已死。
同时,他还发现消费者的“花心”也反映在购买高价或低价产品上。
也就是说,一个消费者有时会买高价产品,有时又会买低价产品。
简单来说,消费者既会买十几块的巴黎气泡水,也会买两块钱的可乐或一块钱的矿泉水。
因为个体的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它由场景决定,并不严格区分。
消费者有时会认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时又会认可“物美价廉”,关键在于自己置身于何种场景,以及什么样的线索启发了相应的决策模式。
因此,夏普教授强调,品牌的关键是做好“大渗透”,而不是去搞人群细分(如高端人群、高端品牌等)。哪怕是奢侈品,也要强调大渗透,让更多人来买。从这个角度看,价格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然而,在营销实践中,我们常常认为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属性,它代表着某种消费者天然的区分。
比如,消费者认知中的多元维生素就应该是一个药片的样子,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做成胶囊或液体,就可能享受不到这种物理属性带来的红利,因为这违背了消费者的常识。你需要花很大力气重新沟通,才能帮消费者建立决策支撑,这纯属吃力不讨好。
价格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物理属性,同样在于消费者在购买场景中的常识感知。
想当年,云南白药刚开始卖它的止血牙膏时,定价二十多块,而当时普通牙膏都在十块左右,所以渠道商普遍不看好它。
但随着竞争加剧,很多领先品牌都推出了大克数的牙膏,其零售价也卖到了二十多块。正是这些大包装产品,让消费者适应了二十多块钱这个“价格物理属性”,才有了云南白药借助这种价格常识,并利用其“止血”特点,迅速扩大渗透率,成为领导品牌。
这种总结可能过于简单,但从价格这个物理属性的角度看,它对消费者个体决策有着重要意义。
在个体决策场景中,价格以物理属性的方式存在,影响着个体的非理性决策。这种常识的改变需要长期适应,无法一蹴而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CBD开发出一个叫“用户流转图”的工具来描述这种状态。
我们可以用一个坐标象限来表达这张图:Y轴分为低价格带和高价格带;X轴则用各种终端形式来描述,比如社区超市、大卖场、便利店、B2C、O2O等。然后,我们可以把各个牙膏品牌填到相应的位置。
比如,我们选择云南白药刚开始推广的时间点,会发现高价位(20多元)的只有它,而其他主流品牌都在低价位(10元左右)。
如果我们愿意把抗过敏牙膏“舒适达”放进去,甚至还可以添加一个“医院”渠道,因为它当年可能是通过医生推荐做起来的,也属于高价格带。
如果我们能每隔五年就做一张这样的图表,就能连续地看到牙膏市场在品牌、价格、终端三个维度上的变化趋势,这相当于一个消费者流转的过程。
我们知道,夏普教授所说的“花心”消费者依然存在,他们有时买贵的,有时买便宜的,这都没关系。
但是,当我们站在群体理性的统计学视角去看时,就会发现,随着时间推移,高价格带牙膏的用户数量或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这代表着一种消费者从低价格带向高价格带的迁徙。
这种迁徙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大家同时推出大包装,可能是高价产品进行了大规模渗透,可能是消费升级,也可能是终端(如超市)想赚更多钱。就像当年国美、苏宁经常会有专属的格力特制款一样,终端为了保证利润空间,可能会要求品牌推出定制款。
再举一个手机的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
苹果一直在高价格带;华为则高、中、低端产品都有;OPPO、vivo相对便宜,但也出了不少中高端产品。
十年前,手机行业进行了一轮残酷的价格战,淘汰了很多品牌。而现在,整个行业都在向高价产品进军。
高价只是一种现象,其背后代表着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为整个生态的利益相关方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才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市场处于专家们所说的“消费降级”状态,因为消费者手里的钱可能有点紧张。
但是,就像当年手机行业的价格战一样,今天各行业所谓的消费降级趋势,并不意味着品牌不需要去思考如何在高价格带提供更好的体验和价值。
恰恰相反,只有掌握了高价格带的市场份额,才能保证企业的利润;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中低价格带进行残酷的市场竞争,淘汰掉那些没有能力的企业和品牌。
在用户流转图中,高价格带的市场份额,其实代表着非理性的个体消费者决定购买高价产品的概率,而不是说有一群固定的消费者聚集在那里。
正是他们的购买概率,形成了一个更有价值、更可持续的市场,也更能帮助品牌穿越周期,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所以,群体理性或个体非理性,只不过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它们看到的都是真相,并无冲突。
就像虽然现在可能是消费降级的环境,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必去考虑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价值。
事实上,它们永远是统一的。这也正是用户流转图想要传达的意义: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只有真正为消费者和整个生态创造价值,整个生态才会欣欣向荣,品牌也才可能在繁荣的生态中,永远向上。

 小程序
扫码打开微信小程序
小程序
扫码打开微信小程序
 APP下载
扫码下载市场部网 App
APP下载
扫码下载市场部网 App